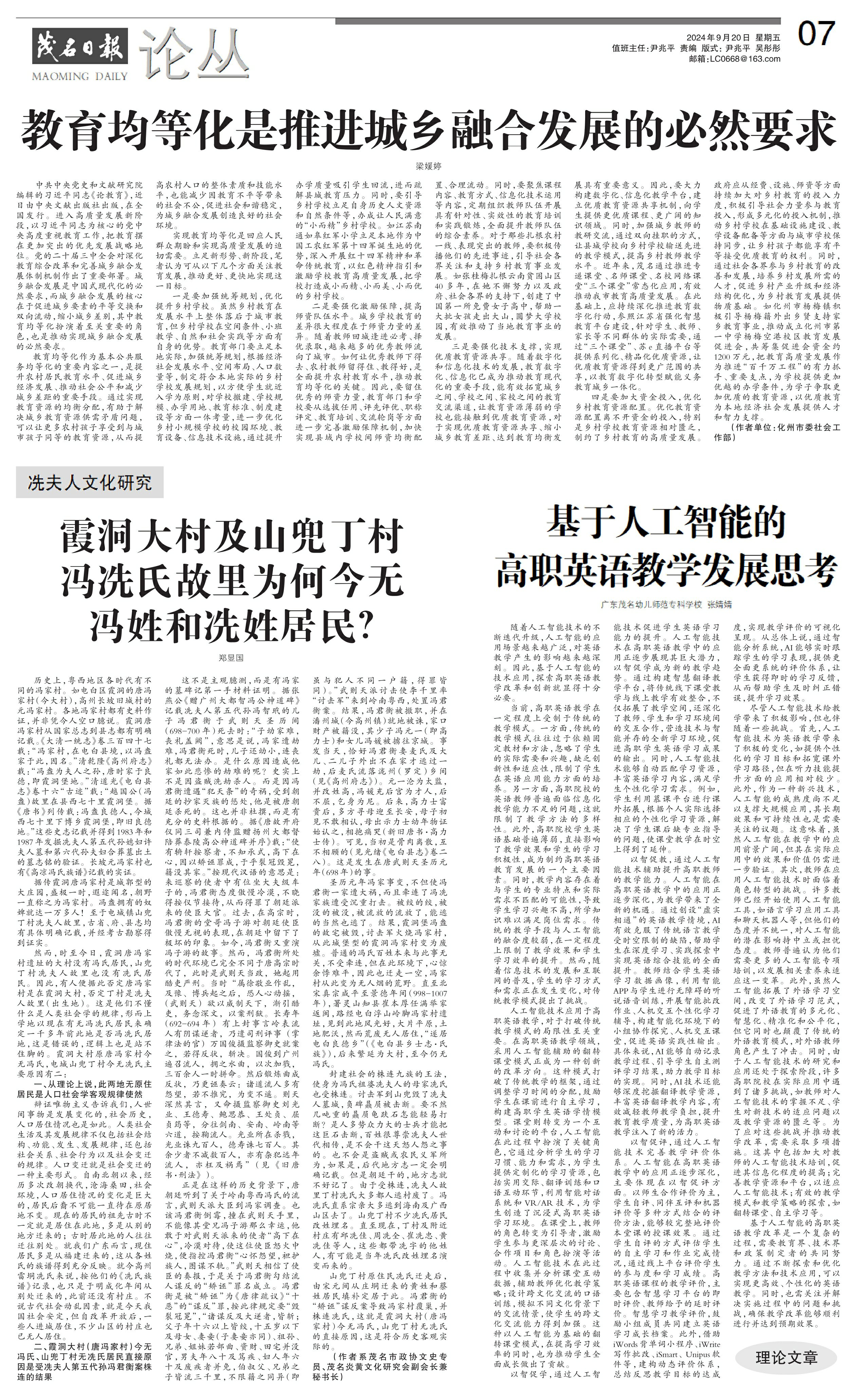冼夫人文化研究
霞洞大村及山兜丁村冯冼氏故里为何今无冯姓和冼姓居民?
郑显国
历史上,粤西地区各时代有不同的冯家村。如电白区霞洞的唐冯家村(今大村),高州长坡旧城村的元冯家村。各地冯家村都有史料作证,并非凭今人空口臆说。霞洞唐冯家村从国家总志到县志都有明确记载。《大清一统志》卷三百四十七载:“冯家村,在电白县境,以冯盎家于此,因名。”清乾隆《高州府志》载:“冯盎为夫人之孙,唐时家于良德,即霞洞堡地。”清道光《电白县志》卷十六“古迹”载:“越国公(冯盎)故里在县西七十里霞洞堡。据《唐书》列传载:冯盎良德人,今城西七十里下博乡霞洞堡,即旧良德地。”这些史志记载并得到1983年和1987年发掘冼夫人第五代孙媳妇许夫人墓和第六代孙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墓志铭的验证。长坡元冯家村也有《高凉冯氏族谱》记载的实证。
据传霞洞唐冯家村是城郭型的大庄园,盛极一时,遐迩闻名,朝野一直称之为冯家村。冯盎拥有的奴婢就达一万多人!至于电城镇山兜丁村冼夫人故里,古省、府、县志均有具体明确记载,并经考古勘察得到证实。
然而,时至今日,霞洞唐冯家村遗址的大村没有冯氏居民,山兜丁村冼夫人故里也没有冼氏居民。因此,有人便据此否定唐冯家村是在霞洞大村,否定丁村是冼夫人故里(出生地)。这是他们不懂什么是人类社会学的规律,形而上学地以现在有无冯冼氏居民来确定一千多年前此地是否冯冼氏居地,这是错误的,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霞洞大村原唐冯家村今无冯氏,电城山兜丁村今无冼氏主要原因有二:
一、从理论上说,此两地无原住居民是人口社会学客观规律使然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世间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社会历史,人口居住情况也是如此。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发展规律不仅包括社会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还包括社会关系、社会行为以及社会变迁的规律。人口变迁就是社会变迁的一种主要形式。自南北朝以来,经历多次改朝换代,沧海桑田,社会环境,人口居住情况的变化是巨大的,居民后裔不可能一直待在原居地不变。现在的居民的祖先古时不一定就是居住在此地,多是从别的地方迁来的;古时居此地的人往往迁往别处。就我们广东而言,现住居民多是从福建迁来的,这从各姓氏的族谱得到充分反映。就今高州雷垌冼氏来说,按他们的《冼氏族谱》记录,也只是于明成化年间从别处迁来的,此前还没有村庄。不说古代社会动乱因素,就是今天我国社会安定,但自改革开放后,一些人进城居住,不少山区的村庄也已无人居住。
二、霞洞大村(唐冯家村)今无冯氏、山兜丁村无冼氏居民直接原因是受冼夫人第五代孙冯君衡案株连的结果
这不是主观臆测,而是有冯家的墓碑记第一手材料证明。据张燕公《赠广州大都智冯公神道碑》记载冼夫人第五代孙冯智玳的儿子冯君衡于武则天圣历间(698-700年)死去时:“子幼家难,丧礼盖阙”,意思是说,冯家遭劫难,冯君衡死时,儿子还幼小,连丧礼都无法办。是什么原因造成他家如此悲惨的劫难的呢?史实上不是因盗贼洗劫杀人。而是因冯君衡遭遇“犯天条”的奇祸,受到朝廷的抄家灭族的惩处,他是被唐朝廷杀死的。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充分的史料根据的。据《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内侍监赠扬州大都督陪葬泰陵高公神道碑并序》载:“使有辀轩按察者,不知承式,高下在心,因以矫诬罪成,于乎裂冠毁冕,籍没其家。”按现代汉语的意思是:来巡察的使者中有位坐大夫级车子的,冯君衡态度傲慢冷漠,不晓得按仪节接待,从而得罪了朝廷派来的使臣大官。过去,在高宗时,冯君衡的堂哥冯子游对朝廷使臣傲慢无视的表现,在朝廷中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如今,冯君衡又重演冯子游的故事。然而,冯君衡所处的时代环境已完全不同于唐高宗时代了,此时是武则天当政,她起用酷吏严刑。当时“属徐敬业作乱,及豫、博兵起之后,恐人心动摇,(武则天)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念深文,以案刑狱。长寿年(692-694年)有上封事言岭表流人有阴谋逆者,乃遣司刑评事(掌律法的官)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状,斩决。国俊到广州遍召流人,拥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余人一时拼命。然后锻炼曲成反状,乃更诬奏云:诸道流人多有怨望,若不推究,为变不遥。则天深然其言,又命摄监察御史刘光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处贞、屈贞筠等,分往剑南、安南、岭南等六道,按鞠流人。光业所在杀戮,光业诛九百人,德寿诛七百人。其余少者不减数百人,亦有杂犯远年流人,亦枉及祸焉”(见《旧唐书·刑法》)。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唐朝廷听到了关于岭南粤西冯氏的流言,武则天派大臣到冯家调查。也该冯君衡倒霉,撞在武则天手里,不能像其堂兄冯子游那么幸运,他敢于对武则天派来的使者“高下在心”,冷漠对待,使这位使臣怒火中烧,便指控冯君衡“心怀怨望,袒护族人,图谋不轨。”武则天相信了使臣的奏报,于是关于冯君衡勾结流人谋反的“矫诬”罪名成立。冯君衡是被“矫诬”为《唐律疏议》“十恶”的“谋反”罪,按此律规定要“毁裂冠冕”,“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姐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即虽与犯人不同一户籍,得罪皆同)。”武则天派讨击使李千里率“讨击军”来到岭南粤西,处置冯君衡案。结果,冯君衡被撤职,并在潘州城(今高州镇)就地被诛,家口财产被籍没,其少子冯元一(即高力士)和女儿冯媛被掳往京城。事发当天,恰好冯君衡妻麦氏及大儿、二儿子外出不在家才逃过一劫,后麦氏流落泷州(罗定)乡间(见《高州府志》)。元一沦为太监,并改姓高,冯媛充后宫为才人,后不屈,乞身为尼。后来,高力士富贵后,多方寻母迎至长安,母子初见不敢相认,母出示力士幼年物证始认之,相抱痛哭(新旧唐书·高力士传)。可见,当初是骨肉离散,互不相顾的(见光绪《电白县志》卷二八)。这是发生在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的事。
圣历元年冯家事变,不但使冯君衡一家遭大祸,而且牵连了冯冼家族遭受沉重打击。被绞的绞,被没的被没,被流放的流放了,能逃的当然也逃了。结果,霞洞堡冯盎的故宅被毁,讨击军火烧冯家村,从此城堡型的霞洞冯家村变为废墟。普通的冯氏百姓本来与此事无关,不受牵连,但在此环境下,心惊余悸难平,因此也迁走一空,冯家村从此变为无人烟的荒野。直至北宋真宗咸平至景德年间(998-1007年),署灵山知县崔本厚任满举家返闽,路经电白浮山岭脚冯家村遗址,见到此地风光好,大片平原,土地肥沃,然而荒废无人居住,“遂居电白良德乡”(《电白县乡士志·氏族》),后来繁延为大村,至今仍无冯氏。
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的王法,使身为冯氏祖婆冼夫人的母家冼氏也受株连。讨击军到山兜毁了冼夫人墓城,负碑赑屃被击断。要不然几吨重的赑屃龟趺石怎能轻易打断?是人多势众力大的士兵才能把这巨石击断,百姓很尊崇冼夫人世代相传,是不会干这天怒人怨之事的。也不会是盗贼或农民义军所为,如果是,后代地方志一定会明确记载。但是朝廷干的,地方志就不好记了。由于受株连,冼夫人故里丁村冼氏大多都人逃村废了。冯冼氏直系宗亲大多逃到海南及广西山区去了。山兜丁村不少冼氏居民改姓埋名。直至现在,丁村及附近村庄有邱冼佳、周冼全、崔冼忠、黄冼佳等人,这些都带冼字的他姓人,有可能是当年冼氏改姓埋名演变而来的。
山兜丁村原住民冼氏迁走后,由宋元间从庄垌迁来的黄姓和蔡姓居民填补定居于此。冯君衡的“矫诬”谋反案导致冯家村覆巢,并株连冼氏,这就是霞洞大村(唐冯家村)今无冯氏,山兜丁村无冼氏的直接原因,这是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专员、茂名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