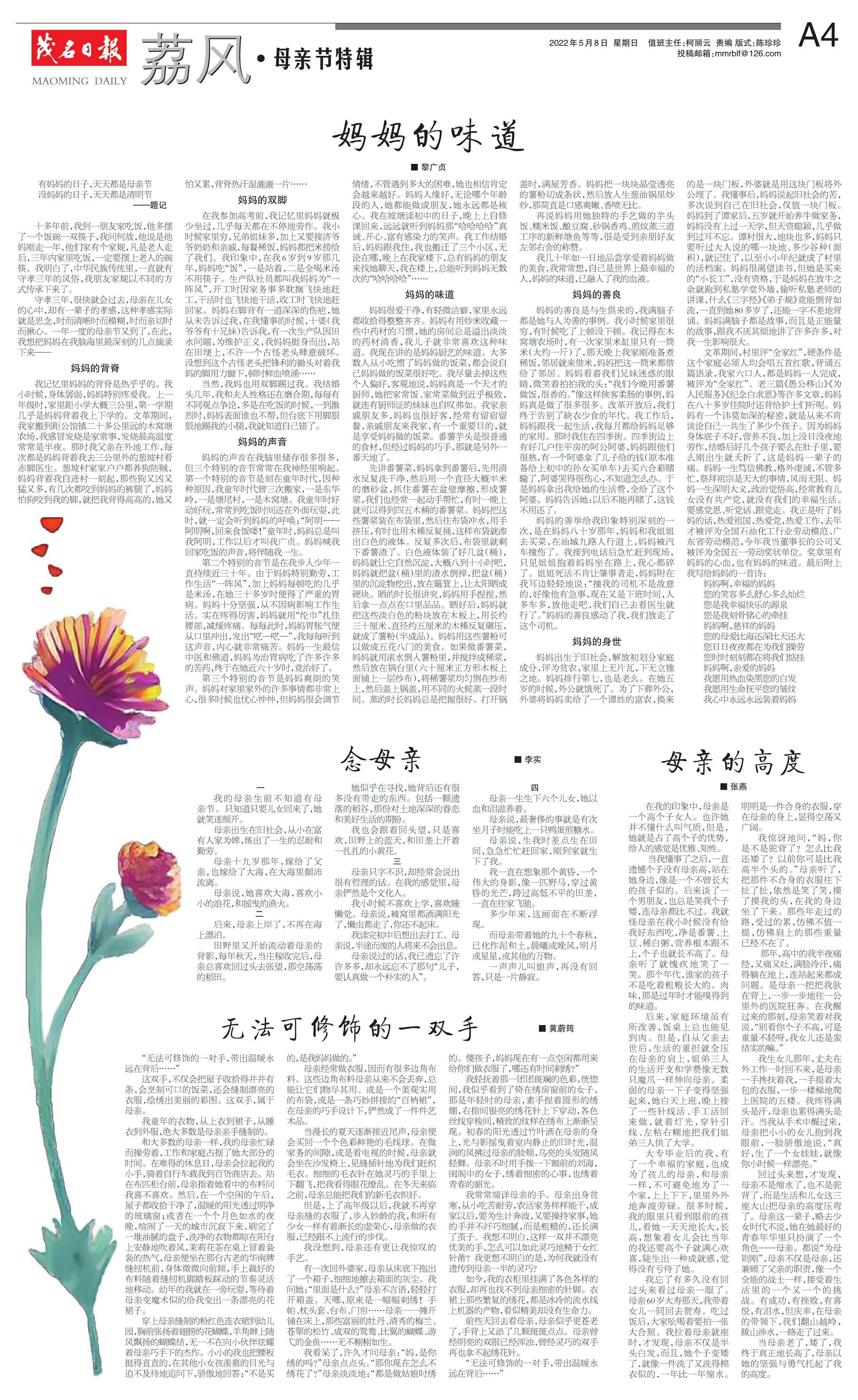无法可修饰的一双手
■黄蔚筠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
这双手,不仅会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会烹制可口的饭菜,还会缝制漂亮的衣服,绘绣出美丽的彩图。这双手,属于母亲。
我童年的衣物,从上衣到裙子,从睡衣到外服,绝大多数是母亲亲手缝制的。
和大多数的母亲一样,我的母亲忙碌而操劳着,工作和家庭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时间。在难得的休息日,母亲会拉起我的小手,骑着自行车载我到百货商店去。站在布匹柜台前,母亲指着她看中的布料问我喜不喜欢。然后,在一个空闲的午后,屋子都收拾干净了,温暖的阳光透过明净的玻璃窗;或者在一个个月色如水的夜晚,喧闹了一天的城市沉寂下来,刷完了一堆油腻的盘子,洗净的衣物都晾在阳台上安静地吹着风,茉莉花茶在桌上冒着袅袅的热气,母亲便坐在那台古老的华南牌缝纫机前,身体微微向前倾,手上裁好的布料随着缝纫机脚踏板踩动的节奏灵活地移动。幼年的我就在一旁玩耍,等待着母亲变魔术似的给我变出一条漂亮的花裙子。
穿上母亲缝制的粉红色连衣裙到幼儿园,胸前张扬着翅膀的花蝴蝶,羊角辫上随风飘扬的蝴蝶结,无一不在向小伙伴炫耀着母亲巧手下的杰作。小小的我也把腰板挺得直直的,在其他小女孩羡慕的目光与迫不及待地追问下,骄傲地回答:“不是买的,是我妈妈做的。”
母亲经常做衣服,因而有很多边角布料。这些边角布料母亲从来不会丢弃,总能让它们物尽其用。或是一个美观实用的布袋,或是一条巧妙拼接的“百衲裙”,在母亲的巧手设计下,俨然成了一件件艺术品。
当漫长的夏天逐渐接近尾声,母亲便会买回一个个色彩鲜艳的毛线球。在做家务的间隙,或是看电视的时候,母亲就会坐在沙发椅上,见缝插针地为我们赶织毛衣。细细的毛衣针在她灵巧的手里上下翻飞,把我看得眼花缭乱。在冬天来临之前,母亲总能把我们的新毛衣织好。
但是,上了高年级以后,我就不再穿母亲缝的衣服了,步入妙龄的我,和所有少女一样有着渐长的虚荣心,母亲做的衣服,已经跟不上流行的步伐。
我没想到,母亲还有更让我惊叹的手艺。
有一次回外婆家,母亲从床底下拖出了一个箱子,细细地擦去箱面的灰尘。我问她:“里面是什么?”母亲不言语,轻轻打开箱盖。天哪,原来是一幅幅刺绣!手帕、枕头套、台布、门帘……母亲一一摊开铺在床上,那些富丽的牡丹、清秀的梅兰、苍翠的松竹、成双的鸳鸯、比翼的蝴蝶、游弋的金鱼……无不栩栩如生。
我看呆了,许久才问母亲:“妈,是你绣的吗?”母亲点点头。“那你现在怎么不绣花了?”母亲淡淡地:“都是做姑娘时绣的。傻孩子,妈妈现在有一点空闲都用来给你们做衣服了,哪还有时间刺绣?”
我轻抚着那一团团斑斓的色彩,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了倚在绣房窗前的女子,那是年轻时的母亲,素手捏着圆形的绣绷,右指间银亮的绣花针上下穿动,各色丝线穿梭间,精致的纹样在绣布上渐渐呈现。初春的阳光透过竹叶洒在母亲的身上,光与影摇曳着室内静止的旧时光,温润的风拂过母亲的脸颊,乌亮的头发随风轻舞。母亲不时用手拨一下额前的刘海,闺阁中的女子,绣着细密的心事,也绣着青春的韶光。
我常常端详母亲的手。母亲出身贫寒,从小吃苦耐劳,农活家务样样能干,成家以后,要为生计奔波,又要操持家事,她的手并不纤巧细腻,而是粗糙的,还长满了茧子。我想不明白,这样一双并不漂亮优美的手,怎么可以如此灵巧地精于女红针黹?我更想不明白的是,为何我就没有遗传到母亲一半的灵巧?
如今,我的衣柜里挂满了各色各样的衣服,却再也找不到母亲细密的针脚。衣裙上那些繁复的绣花,都是冰冷的流水线上机器的产物,看似精美却没有生命力。
前些天回去看母亲,母亲似乎更苍老了,手背上又添了几颗斑斑点点。母亲曾经明亮的双眼已经浑浊,曾经灵巧的双手再也拿不起绣花针。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