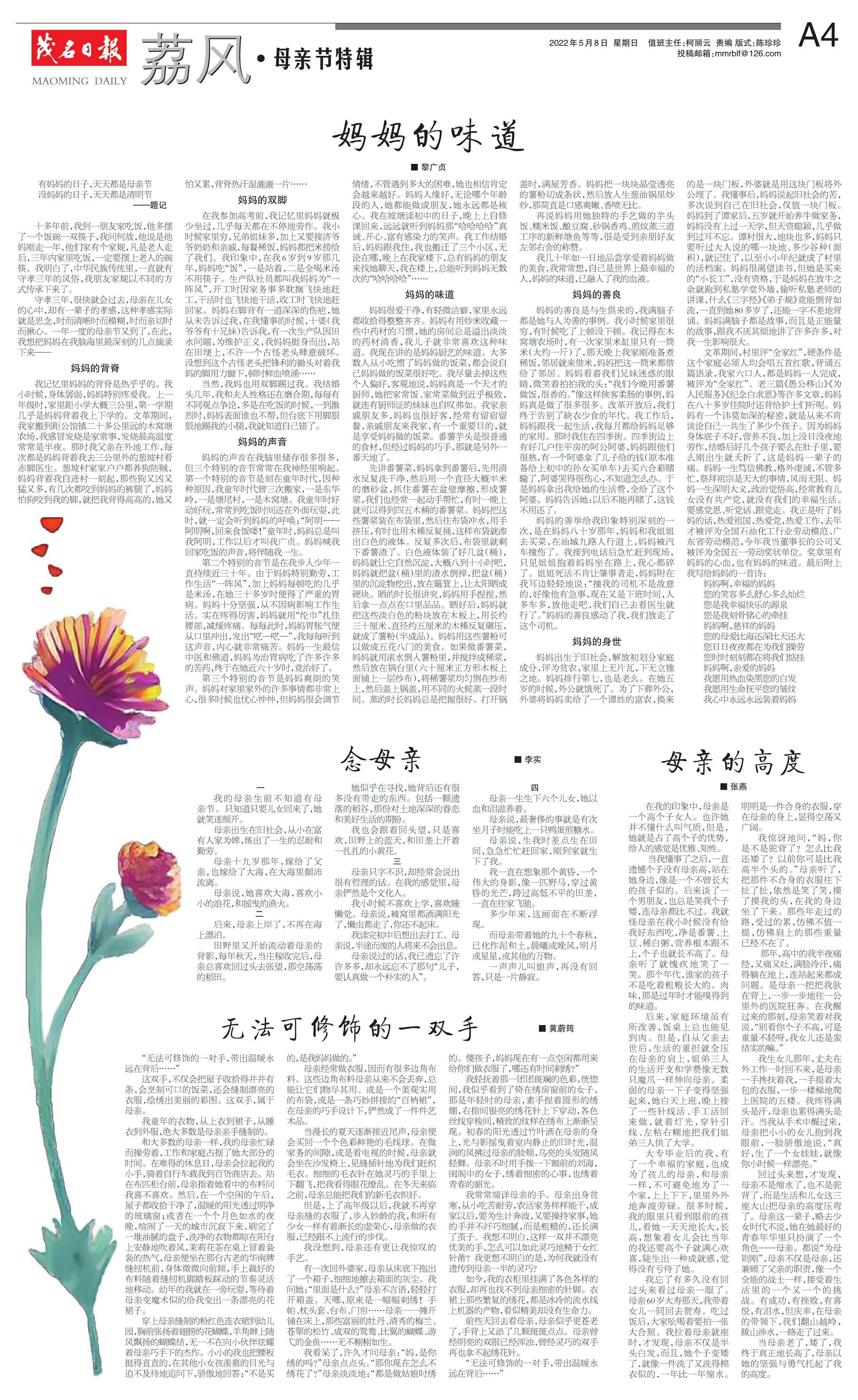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妈妈的味道
■黎广贞
有妈妈的日子,天天都是母亲节没妈妈的日子,天天都是清明节——题记
十多年前,我到一朋友家吃饭,他多摆了一个饭碗一双筷子,我问何故,他说是他妈刚走一年,他们家有个家规,凡是老人走后,三年内家里吃饭,一定要摆上老人的碗筷。我明白了,中华民族传统里,一直就有守孝三年的风俗,我朋友家规以不同的方式传承下来了。
守孝三年,很快就会过去,母亲在儿女的心中,却有一辈子的孝感,这种孝感实际就是思念,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时而亲切时而揪心。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又到了,在此,我想把妈妈在我脑海里最深刻的几点摘录下来——
妈妈的背脊
我记忆里妈妈的背脊是热乎乎的。我小时候,身体孱弱,妈妈特别疼爱我。上一年级时,家里距小学大概三公里,第一学期几乎是妈妈背着我上下学的。文革期间,我家搬到距公馆镇二十多公里远的木窝塘农场,我感冒发烧是家常事,发烧最高温度常常是半夜。那时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每次都是妈妈背着我去三公里外的葱坡村看赤脚医生。葱坡村家家户户都养狗防贼,妈妈背着我自进村一刻起,那些狗又凶又猛又多,有几次都咬到妈妈的裤腿了,妈妈怕狗咬到我的脚,就把我背得高高的,她又怕又累,背脊热汗湿漉漉一片……
妈妈的双脚
在我参加高考前,我记忆里妈妈就极少坐过,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劳作。我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姐妹多,加上又要接济爷爷奶奶和亲戚,每餐稀饭,妈妈都把米捞给了我们。我印象中,在我6岁到9岁那几年,妈妈吃“饭”,一是站着,二是全喝米汤不用筷子。生产队社员都叫我妈妈为“一阵风”,开工时因家务事多耽搁飞快地赶工,干活时也飞快地干活,收工时飞快地赶回家。妈妈右脚背有一道深深的伤疤,她从未告诉过我,在我懂事的时候,十婆(我爷爷有十兄妹)告诉我,有一次生产队因田水问题,为维护正义,我妈妈挺身而出,站在田埂上,不许一个古怪老头肆意破坏。没想到这个古怪老头把锋利的锄头对着我妈的脚用力锄下,顿时鲜血喷涌……
当然,我妈也用双脚踢过我。我结婚头几年,我和夫人性格还在磨合期,每每有不同观点争论,多是在吃饭的时候,一到激烈时,妈妈表面谁也不帮,但台底下用脚狠狠地踢我的小腿,我就知道自己错了。
妈妈的声音
妈妈的声音在我脑里储存很多很多,但三个特别的音节常常在我神经里响起。第一个特别的音节是刻在童年时代,因种种原因,我童年时代曾三次搬家,一是东华岭,一是塘尾村,一是木窝塘。我童年时好动好玩,常常到吃饭时间还在外面玩耍,此时,就一定会听到妈妈的呼唤:“阿明——阿明啊,回来食饭喽!”童年时,妈妈总是叫我阿明,工作以后才叫我广贞。妈妈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将伴随我一生。
第二个特别的音节是在我步入少年一直持续近三十年。由于妈妈特别勤劳,工作生活“一阵风”,加上妈妈每顿吃的几乎是米汤,在她三十多岁时便得了严重的胃病。妈妈十分坚强,从不因病影响工作生活。实在疼得厉害,妈妈就用“纶巾”扎住腰部,减缓疼痛。每每此时,妈妈胃胀气便从口里冲出,发出“呓—呓—”,我每每听到这声音,内心就非常痛苦。妈妈一生最信中医和佛道,妈妈为治胃病吃了许多许多的苦药,终于在她近六十岁时,竟治好了。
第三个特别的音节是妈妈爽朗的笑声。妈妈对家里家外的许多事情都非常上心,很多时候也忧心忡忡,但妈妈很会调节情绪,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她也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好。妈妈人缘好,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她都能做成朋友,她永远都是核心。我在坡塘读初中的日子,晚上上自修课回来,远远就听到妈妈那“哈哈哈哈”真诚、开心、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我工作结婚后,妈妈跟我住,我也搬迁了三个小区,无论在哪,晚上在我家楼下,总有妈妈的朋友来找她聊天,我在楼上,总能听到妈妈无数次的“哈哈哈哈”……
妈妈的味道
妈妈很爱干净,有轻微洁癖,家里永远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妈妈有用炒米收藏一些中药材的习惯,她的房间总是溢出淡淡的药材清香,我儿子就非常喜欢这种味道。我现在讲的是妈妈厨艺的味道。大多数人从小吃惯了妈妈做的饭菜,都会说自己妈妈做的饭菜很好吃。我尽量去掉这些个人偏好,客观地说,妈妈真是一个天才的厨师,她把家常饭、家常菜做到近乎极致,就连有厨师证的妹妹也自叹弗如。我家亲戚朋友多,妈妈也很好客,经常有留宿留餐,亲戚朋友来我家,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享受妈妈做的饭菜。番薯芋头是很普通的食材,但经过妈妈的巧手,那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了。
先讲番薯菜,妈妈拿到番薯后,先用清水反复洗干净,然后用一个直径大概半米的磨砂盆,抓住番薯在盆壁摩擦,形成薯浆,我们也经常一起动手帮忙,有时一晚上就可以得到四五木桶的番薯浆。妈妈把这些薯浆装在布袋里,然后往布袋冲水,用手挤压,有时也用木棒反复捅,这样布袋就渗出白色的液体。反复多次后,布袋里就剩下番薯渣了。白色液体装了好几盆(桶),妈妈就让它自然沉淀,大概八到十小时吧,妈妈就把盆(桶)里的渣水倒掉,把盆(桶)里的沉淀物挖出,放在簸箕上,让太阳晒成硬块。晒的时长很讲究,妈妈用手捏捏,然后拿一点点在口里品品。晒好后,妈妈就把这些淡白色的粉块放在木板上,用长约三十厘米、直径约五厘米的木棒反复碾压,就成了薯粉(半成品)。妈妈用这些薯粉可以做成五花八门的美食。如果做番薯菜,妈妈就用滚水倒入薯粉里,并搅拌成稀浆,然后放在锅台里(六十厘米正方形木板上面铺上一层纱布),将稀薯浆均匀倒在纱布上,然后盖上锅盖,用不同的火候蒸一段时间。蒸的时长妈妈总是把握很好。打开锅盖时,满屋芳香。妈妈把一块块晶莹透亮的薯粉切成条状,然后放入生葱油锅里炒炒,那简直是口感爽嫩、香喷无比。
再说妈妈用她独特的手艺做的芋头饭、糯米饭、酿豆腐、砂锅香鸡、煎炆蒸三道工序的新鲜塘鱼等等,很是受到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称赞。
我几十年如一日地品尝享受着妈妈做的美食,我常常想,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妈妈的味道,已融入了我的血液。
妈妈的善良
妈妈的善良是与生俱来的,我满脑子都是她与人为善的事例。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有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我记得在木窝塘农场时,有一次家里米缸里只有一筒米(大约一斤)了,那天晚上我家刚准备煮稀饭,邻居就来借米,妈妈把这一筒米都借给了邻居。妈妈看着我们兄妹迷惑的眼睛,微笑着拍拍我的头:“我们今晚用番薯做饭,很香的。”像这样侠客柔肠的事例,妈妈真是做了很多很多。改革开放后,我们终于告别了缺衣少食的年代。我工作后,妈妈跟我一起生活,我每月都给妈妈足够的家用。那时我住在四季街。四季街边上有好几户住平房的阿公阿婆,妈妈跟他们很熟,有一个阿婆拿了儿子给的钱(原本准备给上初中的孙女买单车)去买六合彩赌输了,阿婆哭得很伤心,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妈妈拿出我给她的生活费,全给了这个阿婆。妈妈告诉她:以后不能再赌了,这钱不用还了。
妈妈的善举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是在妈妈八十岁那年,妈妈和我姐姐去买菜,在油城九路人行道上,妈妈被汽车撞伤了。我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到现场,只见姐姐抱着妈妈坐在路上,我心都碎了。姐姐死活不肯让肇事者走,妈妈附在我耳边轻轻地说:“撞我的司机不是故意的,好像他有急事,现在又是下班时间,人多车多,放他走吧,我们自己去看医生就行了。”妈妈的善良感动了我,我们放走了这个司机。
妈妈的身世
妈妈出生于旧社会,解放初划分家庭成分,评为贫农,家里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妈妈排行第七,也是老幺。在她五岁的时候,外公就饿死了。为了下葬外公,外婆将妈妈卖给了一个谭姓的富农,换来的是一块门板,外婆就是用这块门板将外公埋了。我懂事后,妈妈说起旧社会的苦,多次说到自己在旧社会,仅值一块门板。妈妈到了谭家后,五岁就开始养牛做家务,妈妈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天资聪颖,几乎做到过耳不忘。谭村很大,地块也多,妈妈只要听过大人说的哪一块地、多少谷种(面积),就记住了,以至小小年纪就成了村里的活档案。妈妈很渴望读书,但她是买来的“小长工”,没有资格,于是妈妈在放牛之余就跑到私塾学堂外墙,偷听私塾老师的讲课,什么《三字经》《弟子规》竟能倒背如流,一直到她80多岁了,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妈妈满脑子都是故事,而且是正能量的故事,跟我不厌其烦地讲了许多许多,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文革期间,村里评“全家红”,硬条件是这个家庭必须人均会唱五首红歌,背诵五篇语录,我家六口人,都是妈妈一人完成,被评为“全家红”。老三篇《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许多文章,妈妈在八十多岁住院时还背给护士们听呢。妈妈有一个讳莫如深的秘密,就是从来不肯谈论自己一共生了多少个孩子。因为妈妈身体底子不好,营养不良,加上没日没夜地劳作,结婚后好几个孩子要么在肚子里,要么刚出生就夭折了,这是妈妈一辈子的痛。妈妈一生笃信佛教,格外虔诚,不管多忙,祭拜祖宗是天大的事情,风雨无阻。妈妈一生深明大义,政治觉悟高,经常教育儿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我正是听了妈妈的话,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工作,去年才被评为全国石油化工行业劳动模范、广东省劳动模范,今年我当董事长的公司又被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单位。奖章里有妈妈的心血,也有妈妈的味道。最后附上我写给妈妈的一首诗:
妈妈啊,幸福的妈妈
您的笑容多么舒心多么灿烂
您是我幸福快乐的源泉
您是我刻骨铭心的牵挂
妈妈啊,慈祥的妈妈
您的母爱比海还深比天还大
您日日夜夜都在为我们操劳
您时时刻刻都在将我们惦挂
妈妈啊,亲爱的妈妈
我愿用热血染黑您的白发
我愿用生命抚平您的皱纹
我心中永远永远装着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