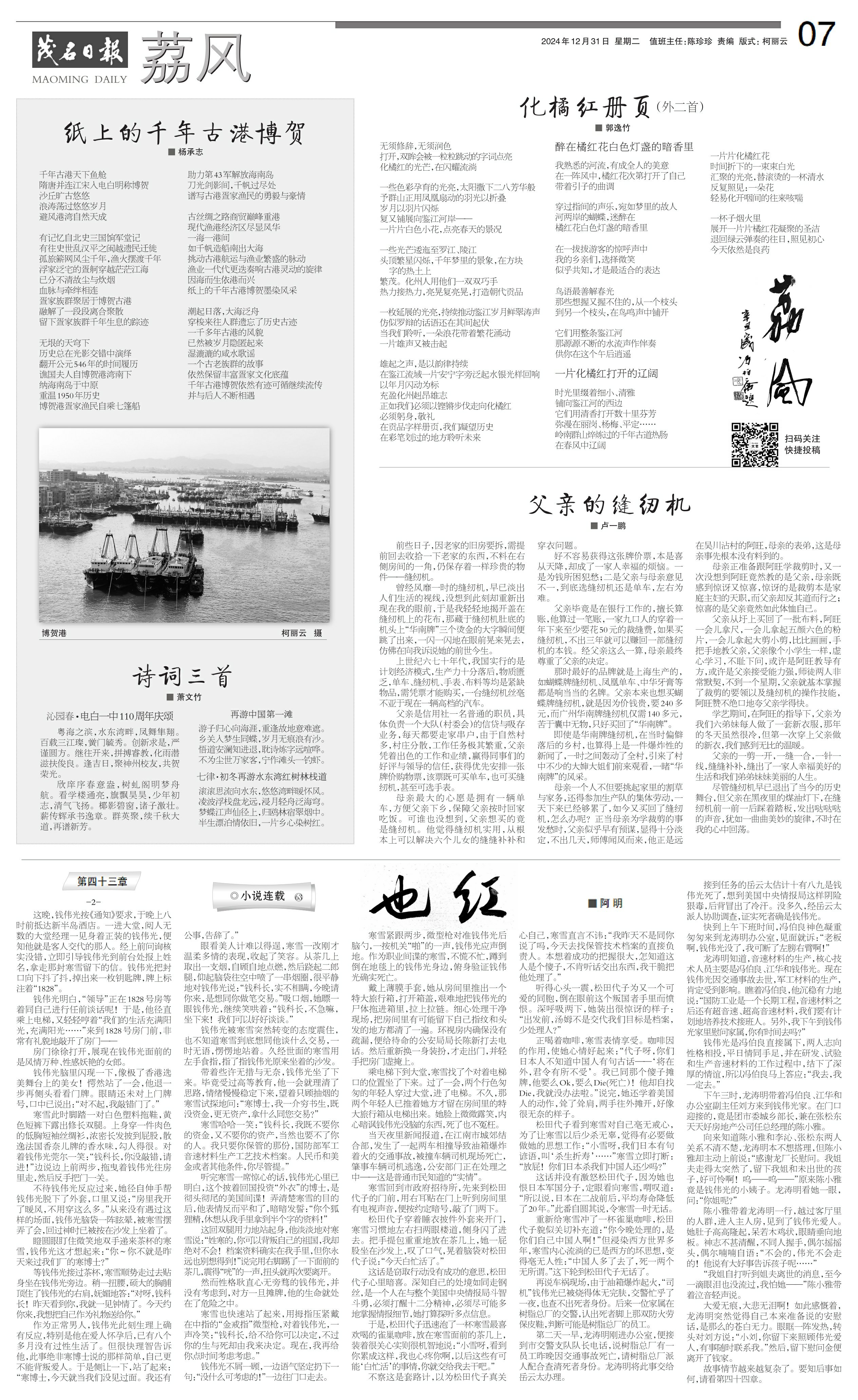父亲的缝纫机
■卢一鹏
前些日子,因老家的旧房要拆,需提前回去收拾一下老家的东西,不料在右侧房间的一角,仍保存着一样珍贵的物件——缝纫机。
曾经风靡一时的缝纫机,早已淡出人们生活的视线,没想到此刻却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我轻轻地揭开盖在缝纫机上的花布,那藏于缝纫机肚底的机头上“华南牌”三个烫金的大字瞬间便跳了出来,一闪一闪地在眼前晃来晃去,仿佛在向我诉说她的前世今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生产力十分落后,物质匮乏,单车、缝纫机、手表、布料等均是紧缺物品,需凭票才能购买,一台缝纫机丝毫不亚于现在一辆高档的汽车。
父亲是信用社一名普通的职员,具体负责一个大队(村委会)的信贷与吸存业务,每天都要走家串户,由于自然村多,村庄分散,工作任务极其繁重,父亲凭着出色的工作和业绩,赢得同事们的好评与领导的信任,获得优先安排一张牌价购物票,该票既可买单车,也可买缝纫机,甚至可选手表。
母亲最大的心愿是拥有一辆单车,方便父亲下乡,保障父亲按时回家吃饭。可谁也没想到,父亲想买的竟是缝纫机。他觉得缝纫机实用,从根本上可以解决六个儿女的缝缝补补和穿衣问题。
好不容易获得这张牌价票,本是喜从天降,却成了一家人幸福的烦恼。一是为钱所困犯愁;二是父亲与母亲意见不一,到底选缝纫机还是单车,左右为难。
父亲毕竟是在银行工作的,擅长算账,他算过一笔账,一家九口人的穿着一年下来至少要花50元的裁缝费,如果买缝纫机,不出三年就可以赚回一部缝纫机的本钱。经父亲这么一算,母亲最终尊重了父亲的决定。
那时最好的品牌就是上海生产的,如蝴蝶牌缝纫机、凤凰单车、中华牙膏等都是响当当的名牌。父亲本来也想买蝴蝶牌缝纫机,就是因为价钱贵,要240多元,而广州华南牌缝纫机仅需140多元,苦于囊中无物,只好买回了“华南牌”。
即使是华南牌缝纫机,在当时偏僻落后的乡村,也算得上是一件爆炸性的新闻了,一时之间轰动了全村,引来了村中不少的大婶大姐们前来观看,一睹“华南牌”的风采。
母亲一个人不但要挑起家里的割草与家务,还得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一天下来已经够累了,如今又买回了缝纫机,怎么办呢?正当母亲为学裁剪的事发愁时,父亲似乎早有预谋,显得十分淡定,不出几天,师傅闻风而来,他正是远在吴川沾村的阿旺,母亲的表弟,这是母亲事先根本没有料到的。
母亲正准备跟阿旺学裁剪时,又一次没想到阿旺竟然教的是父亲,母亲既感到惊讶又惊喜,惊讶的是裁剪本是家庭主妇的天职,而父亲却反其道而行之;惊喜的是父亲竟然如此体恤自己。
父亲从圩上买回了一批布料,阿旺一会儿拿尺,一会儿拿起五颜六色的粉片,一会儿拿起大剪小剪,比比画画,手把手地教父亲,父亲像个小学生一样,虚心学习,不耻下问,或许是阿旺教导有方,或许是父亲接受能力强,师徒两人非常默契,不到一个星期,父亲就基本掌握了裁剪的要领以及缝纫机的操作技能,阿旺赞不绝口地夸父亲学得快。
学艺期间,在阿旺的指导下,父亲为我们六弟妹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那年的冬天虽然很冷,但第一次穿上父亲做的新衣,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
父亲的一剪一开,一缝一合,一针一线,缝缝补补,缝出了一家人幸福美好的生活和我们弟弟妹妹美丽的人生。
尽管缝纫机早已退出了当今的历史舞台,但父亲在黑夜里的煤油灯下,在缝纫机前一前一后踩着踏板,发出哒哒哒的声音,犹如一曲曲美妙的旋律,不时在我的心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