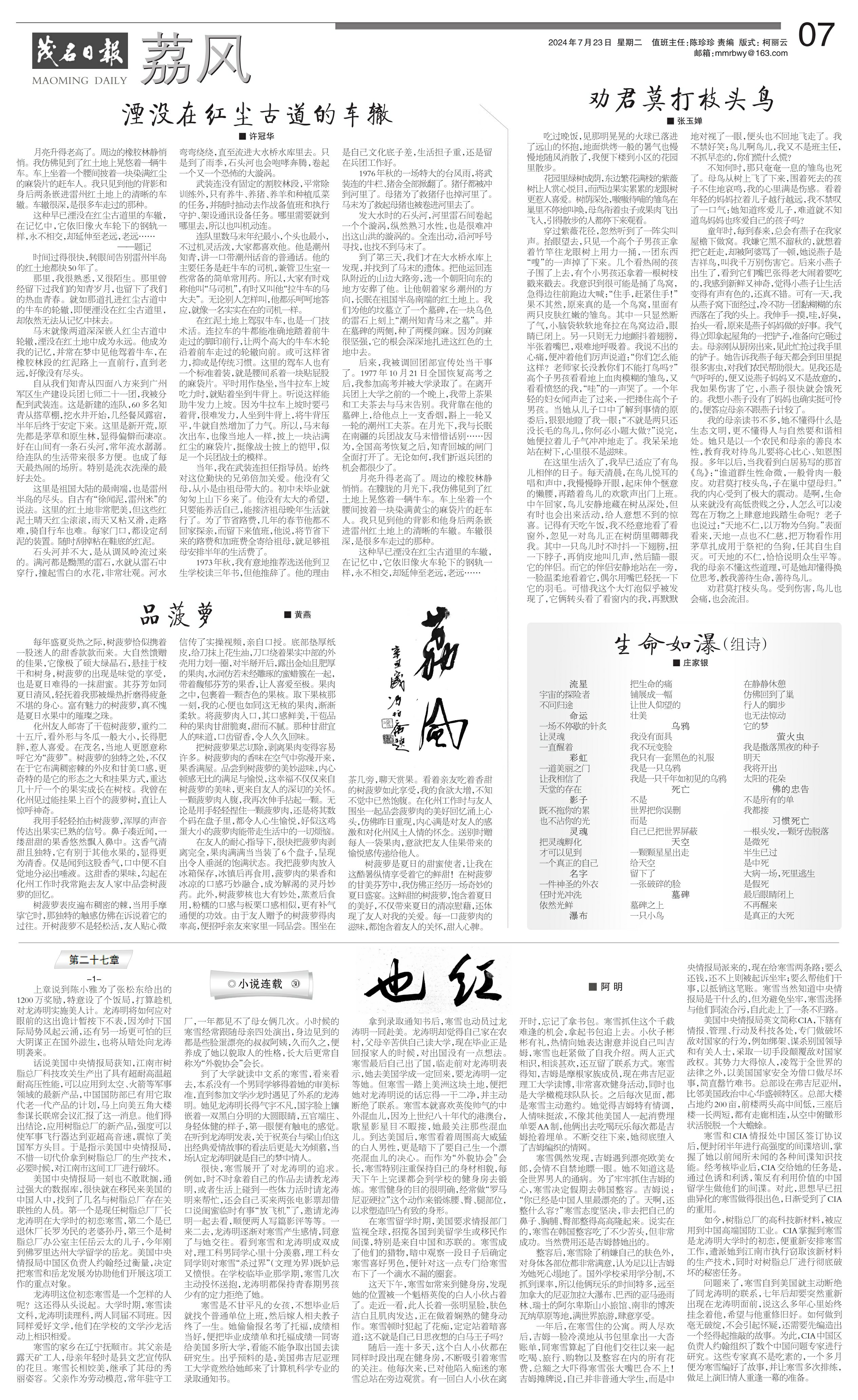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湮没在红尘古道的车辙
■许冠华
月亮升得老高了。周边的橡胶林静悄悄。我仿佛见到了红土地上晃悠着一辆牛车。车上坐着一个腰间披着一块染满红尘的麻袋片的赶车人。我只见到他的背影和身后两条嵌进雷州红土地上的清晰的车辙。车辙很深,是很多车走过的那种。
这种早已湮没在红尘古道里的车辙,在记忆中,它依旧像火车轮下的钢轨一样,永不相交,却延伸至老远,老远……
——题记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告别雷州半岛的红土地都快50年了。
那里,我很熟悉,又很陌生。那里曾经留下过我们的知青岁月,也留下了我们的热血青春。就如那道扎进红尘古道中的牛车的轮辙,即便湮没在红尘古道里,却依然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马末就像两道深深嵌入红尘古道中轮辙,湮没在红土地中成为永远。他成为我的记忆,并常在梦中见他驾着牛车,在橡胶林段的红泥路上一直前行,直到老远,好像没有尽头。
自从我们知青从四面八方来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七师二十一团,我被分配到武装连。这是新建的连队,60多名知青从搭草棚,挖水井开始,几经餐风露宿,半年后终于安定下来。这里是新开荒,原先都是茅草和原生林,显得偏僻而凄凉。好在山间有一条石头河,常年流水潺潺。给连队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也成了每天最热闹的场所。特别是洗衣洗澡的最好去处。
这里是祖国大陆的最南端,也是雷州半岛的尽头。自古有“徐闻泥,雷州米”的说法。这里的红土地非常肥美,但这些红泥土晴天红尘滚滚,雨天又粘又滑,走路难,骑自行车也难。每家门口,都设定刮泥的装置。随时刮掉粘在鞋底的红泥。
石头河并不大,是从调风岭流过来的。满河都是黝黑的雷石,水就从雷石中穿行,撞起雪白的水花,非常壮观。河水弯弯绕绕,直至流进大水桥水库里去。只是到了雨季,石头河也会咆哮奔腾,卷起一个又一个恐怖的大漩涡。
武装连没有固定的割胶林段,平常除训练外,只有养牛、养猪、养羊和种植瓜菜的任务,并随时抽动去作战备值班和执行守护、架设通讯设备任务。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所以也叫机动连。
连队里数马末年纪最小,个头也最小,不过机灵活泼,大家都喜欢他。他是潮州知青,讲一口带潮州话音的普通话。他的主要任务是赶牛车的司机,兼管卫生室一些常备的简单常用药。所以,大家有时戏称他叫“马司机”,有时又叫他“拉牛车的马大夫”。无论别人怎样叫,他都乐呵呵地答应,就像一名实实在在的司机一样。
在红泥土地上驾驭牛车,也是一门技术活。连拉车的牛都能准确地踏着前牛走过的脚印前行,让两个高大的牛车木轮沿着前车走过的轮辙向前。或可这样省力,抑或是传统习惯。这里的驾车人也有一个标准着装,就是腰间系着一块贴屁股的麻袋片。平时用作垫坐,当牛拉车上坡吃力时,就贴着坐到牛背上。听说这样能助牛发力上坡。因为牛拉车上坡时要弓着背,很难发力,人坐到牛背上,将牛背压平,牛就自然增加了力气。所以,马末每次出车,也像当地人一样,披上一块沾满红尘的麻袋片,挺像战士披上的铠甲,似足一个兵团战士的模样。
当年,我在武装连担任指导员。始终对这位勤快的兄弟倍加关爱。他没有父母,从小是由祖母带大的。初中未毕业就匆匆上山下乡来了。他没有太大的希望,只要能养活自己,能接济祖母晚年生活就行了。为了节省路费,几年的春节他都不回家探亲,而留下来值班,他说,将节省下来的路费和加班费全寄给祖母,就足够祖母安排半年的生活费了。
1973年秋,我有意地推荐选送他到卫生学校读三年书,但他推辞了。他的理由是自己文化底子差,生活担子重,还是留在兵团工作好。
1976年秋的一场特大的台风雨,将武装连的牛栏、猪舍全部掀翻了。猪仔都被冲到河里了。母猪为了救猪仔也掉河里了。马末为了救起母猪也被卷进河里去了。
发大水时的石头河,河里雷石间卷起一个个漩涡,纵然熟习水性,也是很难冲出这山洪的漩涡的。全连出动,沿河呼号寻找,也找不到马末了。
到了第三天,我们才在大水桥水库上发现,并找到了马末的遗体。把他运回连队附近的山边大路旁,选一个朝阳向东的地方安葬了他。让他朝着家乡潮州的方向,长眠在祖国半岛南端的红土地上。我们为他的坟墓立了一个墓碑,在一块乌色的雷石上刻上“潮州知青马末之墓”。并在墓碑的两侧,种了两棵剑麻。因为剑麻很坚强,它的根会深深地扎进这红色的土地中去。
后来,我被调回团部宣传处当干事了。1977年10月21日全国恢复高考之后,我参加高考并被大学录取了。在离开兵团上大学之前的一个晚上,我带上茶果和工夫茶去与马末告别。我背靠在他的墓碑上,给他点上一支香烟,斟上一轮又一轮的潮州工夫茶。在月光下,我与长眠在南疆的兵团战友马末惜惜话别……因为,全国高考恢复之后,知青回城的闸门全面打开了。无论如何,我们折返兵团的机会都很少了。
月亮升得老高了。周边的橡胶林静悄悄。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仿佛见到了红土地上晃悠着一辆牛车。车上坐着一个腰间披着一块染满黄尘的麻袋片的赶车人。我只见到他的背影和他身后两条嵌进雷州红土地上的清晰的车辙。车辙很深,是很多车走过的那种。
这种早已湮没在红尘古道里的车辙,在记忆中,它依旧像火车轮下的钢轨一样,永不相交,却延伸至老远,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