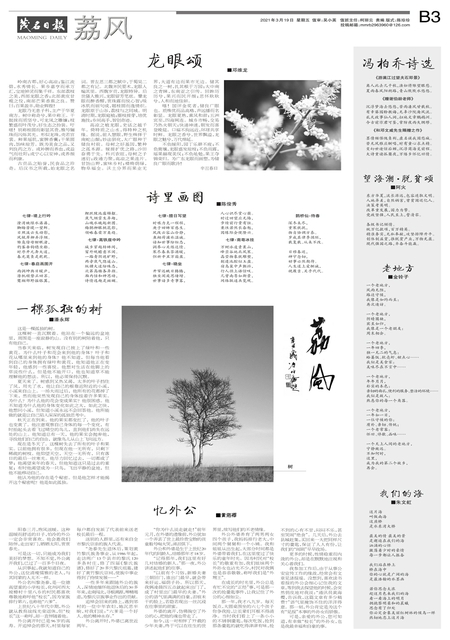忆外公
■黄海樱
阳春三月,煦风送暖。这种温暖而舒适的日子,怕冷的外公一定会非常喜欢。他会邀我们陪伴,走出家门,晒晒太阳,赏赏春光。
可是这一切,只能成为我们美好的梦想。不知不觉,外公离开我们,已过了一百多个日夜。
从识事起,我就知道自己的外公,这位清瘦儒雅的老人,与其同辈的人太不一样。
外公名叫黎尧泰,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小学校长,化州河西大坡樟村十里八乡的村民都喜欢尊敬地称呼他“校长”,因为家族排行第六,也称他“六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外公就从教育战线光荣退休,但“校长”这一称呼,却一直伴随着他。
外公离开时已是96岁的高寿。开追悼会的那天,村里每家每户都自发派了代表前来送老校长最后一程。
送别的人群里,还有来自全市黎氏宗亲的族人代表。
“尧泰先生退休后,策划黄竹黎氏族务事业,从1986年起,走访两广13个县市的黎氏120多条村庄,修了四届《黎氏族谱》,修好了20多穴黎氏祖墓,建好了黄竹黎氏宗祠,使族中事业得到了持续发展……”
一些多年来跟随外公的族人,深情地缅怀他退休后的30多年来,走南闯北,寻根溯源,殚精竭虑,为黎氏宗族事业作出的贡献。
追悼会回来的路上,遇到邻村的一位中年农妇,她沉思半晌,对我们说:“六爹是一个好人,他的精神永存。”
外公离开时,外婆已离世近两年。
“你为什么说走就走!”前年元月,在外婆的遗像前,外公犹如一个弄丢了世上最珍贵宝物的孩童般号啕大哭,涕泪俱下。
外公和外婆是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同龄人,结婚那年才18岁。
“记得那年,我们这里有好几对结婚的新人。”那一夜,外公讲述起他们的往事。
“以前有个习俗,新婚夫妻三朝回门,谁出门最早,就会带来好运,福荫子孙。所以那天,我俩凌晨四五点就起床出门了,成了村里出门最早的夫妻。”外公的语气里满满的自豪,泪痕未干的脸上,若隐若现出一丝沉浸在往事里的甜蜜。
外婆的离开,仿佛掏空了外公的心,把他的魂也带走了。
如今,这一对相伴了77载的少年夫妻,终于可以在往生的世界里,续写他们的不老情缘。
外公外婆养育了两男两女四个孩子,我妈妈排行老大,中间两个舅舅和一个小姨。我和姐姐从出生起,大部分时间都是外婆带着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因为村民对“校长”的敬重有加,我们姐妹两个外孙女也沾光不少,村民对我俩也是恭恭敬敬,称呼我们是“外甥王”。
在成长的时光里,外公总是有忙不完的“正经”事,可是那一次的抢羹匙事件,让我记住了外公的心细如尘。
那一年,我才八九岁。每天饭点,大圆桌围坐的六七个孩子你争我抢,让长辈们耳根不得清净。当时我们看上了一条小小的不锈钢羹匙,每次吃饭,抢到那条羹匙的就吃得津津有味,抢不到的心有不甘,闷闷不乐,甚至哭闹“绝食”。几天后,外公去县城赶集,买回来一大把同样尺寸的羹匙,保证了人人有份,让我们的“闹剧”早早收场。
更多的时候,性情稳重而内敛的外公,却是在默默地注视和关心着我们。
我参加工作后,由于从事公安宣传工作的缘故,经常会有文章见诸报端。没想到,喜欢读书看报的外公会细心记住我的文章,等到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会突然俏皮地对我说:“通讯员黄海樱,告诉我,这篇文章有多少稿费?”语气里掩饰不住的洋洋得意。那一刻,外公肯定是为这个有“见报”本事的外孙女而骄傲。
可是,亲爱的外公,您可知道,有幸做“校长”的外孙女,也是我最幸福和自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