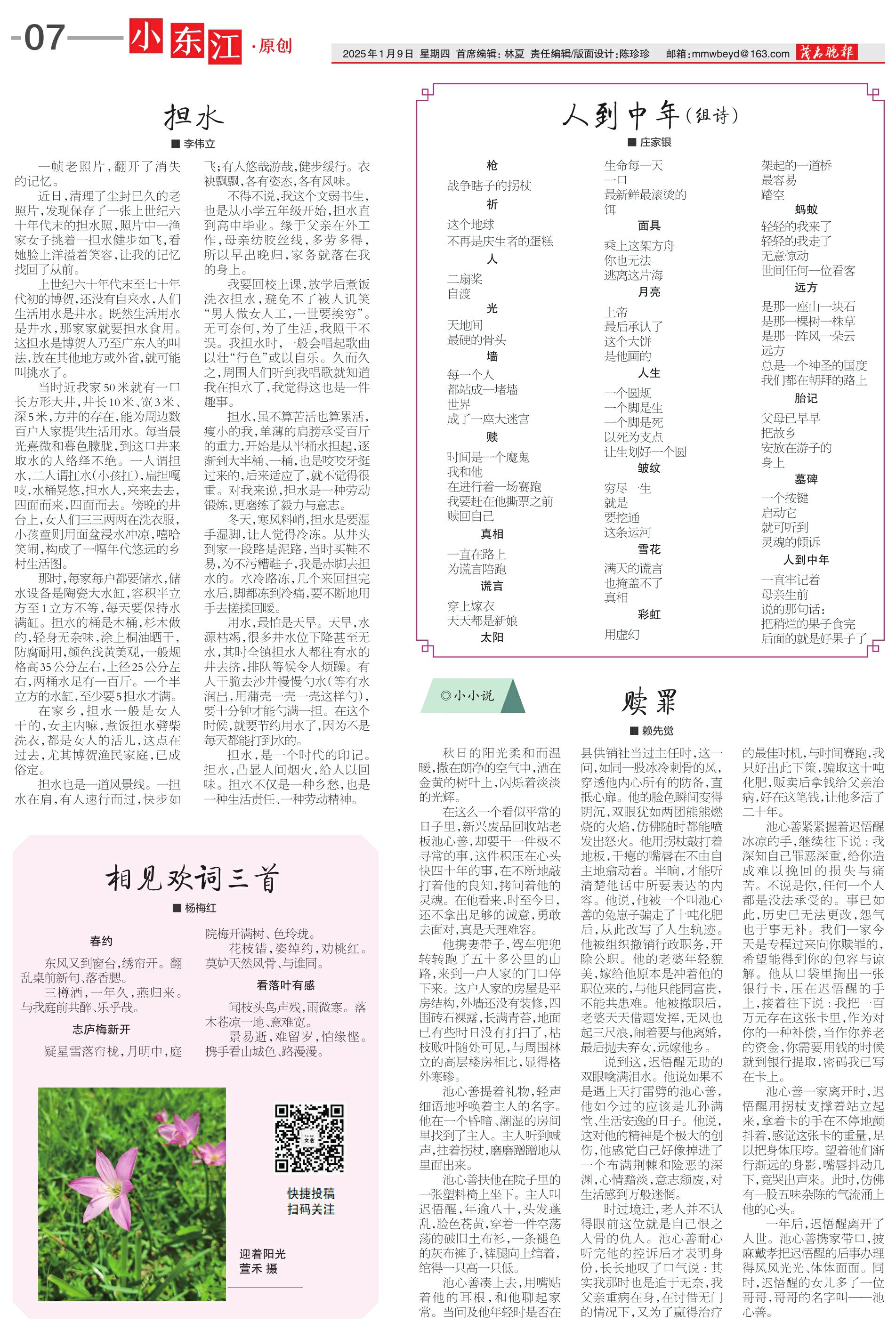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担水
■李伟立
一帧老照片,翻开了消失的记忆。
近日,清理了尘封已久的老照片,发现保存了一张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担水照,照片中一渔家女子挑着一担水健步如飞,看她脸上洋溢着笑容,让我的记忆找回了从前。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博贺,还没有自来水,人们生活用水是井水。既然生活用水是井水,那家家就要担水食用。这担水是博贺人乃至广东人的叫法,放在其他地方或外省,就可能叫挑水了。
当时近我家50米就有一口长方形大井,井长10米、宽3米、深5米,方井的存在,能为周边数百户人家提供生活用水。每当晨光熹微和暮色朦胧,到这口井来取水的人络绎不绝。一人谓担水,二人谓扛水(小孩扛),扁担嘎吱,水桶晃悠,担水人,来来去去,四面而来,四面而去。傍晚的井台上,女人们三三两两在洗衣服,小孩童则用面盆浸水冲凉,嘻哈笑闹,构成了一幅年代悠远的乡村生活图。
那时,每家每户都要储水,储水设备是陶瓷大水缸,容积半立方至1立方不等,每天要保持水满缸。担水的桶是木桶,杉木做的,轻身无杂味,涂上桐油晒干,防腐耐用,颜色浅黄美观,一般规格高35公分左右,上径25公分左右,两桶水足有一百斤。一个半立方的水缸,至少要5担水才满。
在家乡,担水一般是女人干的,女主内嘛,煮饭担水劈柴洗衣,都是女人的活儿,这点在过去,尤其博贺渔民家庭,已成俗定。
担水也是一道风景线。一担水在肩,有人速行而过,快步如飞;有人悠哉游哉,健步缓行。衣袂飘飘,各有姿态,各有风味。
不得不说,我这个文弱书生,也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担水直到高中毕业。缘于父亲在外工作,母亲纺胶丝线,多劳多得,所以早出晚归,家务就落在我的身上。
我要回校上课,放学后煮饭洗衣担水,避免不了被人讥笑“男人做女人工,一世要挨穷”。无可奈何,为了生活,我照干不误。我担水时,一般会唱起歌曲以壮“行色”或以自乐。久而久之,周围人们听到我唱歌就知道我在担水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件趣事。
担水,虽不算苦活也算累活,瘦小的我,单薄的肩膀承受百斤的重力,开始是从半桶水担起,逐渐到大半桶、一桶,也是咬咬牙挺过来的,后来适应了,就不觉得很重。对我来说,担水是一种劳动锻炼,更磨练了毅力与意志。
冬天,寒风料峭,担水是要湿手湿脚,让人觉得冷冻。从井头到家一段路是泥路,当时买鞋不易,为不污糟鞋子,我是赤脚去担水的。水冷路冻,几个来回担完水后,脚都冻到冷痛,要不断地用手去搓揉回暖。
用水,最怕是天旱。天旱,水源枯竭,很多井水位下降甚至无水,其时全镇担水人都往有水的井去挤,排队等候令人烦躁。有人干脆去沙井慢慢勺水(等有水润出,用蒲壳一壳一壳这样勺),要十分钟才能勺满一担。在这个时候,就要节约用水了,因为不是每天都能打到水的。
担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担水,凸显人间烟火,给人以回味。担水不仅是一种乡愁,也是一种生活责任、一种劳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