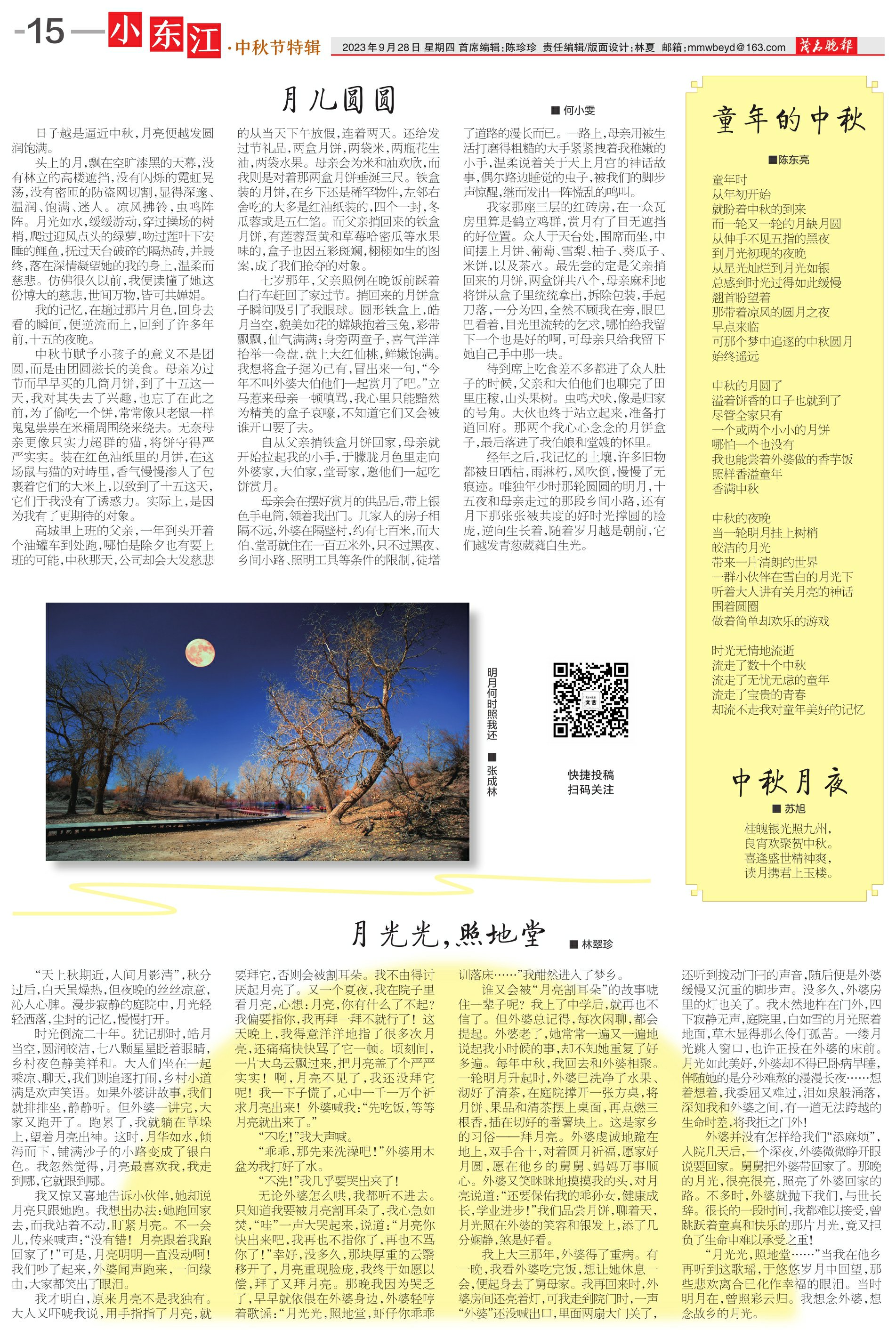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月儿圆圆
■何小雯
日子越是逼近中秋,月亮便越发圆润饱满。
头上的月,飘在空旷漆黑的天幕,没有林立的高楼遮挡,没有闪烁的霓虹晃荡,没有密匝的防盗网切割,显得深邃、温润、饱满、迷人。凉风拂铃,虫鸣阵阵。月光如水,缓缓游动,穿过操场的树梢,爬过迎风点头的绿萝,吻过莲叶下安睡的鲤鱼,抚过天台破碎的隔热砖,并最终,落在深情凝望她的我的身上,温柔而慈悲。仿佛很久以前,我便读懂了她这份博大的慈悲,世间万物,皆可共婵娟。
我的记忆,在趟过那片月色,回身去看的瞬间,便逆流而上,回到了许多年前,十五的夜晚。
中秋节赋予小孩子的意义不是团圆,而是由团圆滋长的美食。母亲为过节而早早买的几筒月饼,到了十五这一天,我对其失去了兴趣,也忘了在此之前,为了偷吃一个饼,常常像只老鼠一样鬼鬼祟祟在米桶周围绕来绕去。无奈母亲更像只实力超群的猫,将饼守得严严实实。装在红色油纸里的月饼,在这场鼠与猫的对峙里,香气慢慢渗入了包裹着它们的大米上,以致到了十五这天,它们于我没有了诱惑力。实际上,是因为我有了更期待的对象。
高城里上班的父亲,一年到头开着个油罐车到处跑,哪怕是除夕也有要上班的可能,中秋那天,公司却会大发慈悲的从当天下午放假,连着两天。还给发过节礼品,两盒月饼,两袋米,两瓶花生油,两袋水果。母亲会为米和油欢欣,而我则是对着那两盒月饼垂涎三尺。铁盒装的月饼,在乡下还是稀罕物件,左邻右舍吃的大多是红油纸装的,四个一封,冬瓜蓉或是五仁馅。而父亲捎回来的铁盒月饼,有莲蓉蛋黄和草莓哈密瓜等水果味的,盒子也因五彩斑斓,栩栩如生的图案,成了我们抢夺的对象。
七岁那年,父亲照例在晚饭前踩着自行车赶回了家过节。捎回来的月饼盒子瞬间吸引了我眼球。圆形铁盒上,皓月当空,貌美如花的嫦娥抱着玉兔,彩带飘飘,仙气满满;身旁两童子,喜气洋洋抬举一金盘,盘上大红仙桃,鲜嫩饱满。我想将盒子据为己有,冒出来一句,“今年不叫外婆大伯他们一起赏月了吧。”立马惹来母亲一顿嗔骂,我心里只能黯然为精美的盒子哀嚎,不知道它们又会被谁开口要了去。
自从父亲捎铁盒月饼回家,母亲就开始拉起我的小手,于朦胧月色里走向外婆家,大伯家,堂哥家,邀他们一起吃饼赏月。
母亲会在摆好赏月的供品后,带上银色手电筒,领着我出门。几家人的房子相隔不远,外婆在隔壁村,约有七百米,而大伯、堂哥就住在一百五米外,只不过黑夜、乡间小路、照明工具等条件的限制,徒增了道路的漫长而已。一路上,母亲用被生活打磨得粗糙的大手紧紧拽着我稚嫩的小手,温柔说着关于天上月宫的神话故事,偶尔路边睡觉的虫子,被我们的脚步声惊醒,继而发出一阵慌乱的鸣叫。
我家那座三层的红砖房,在一众瓦房里算是鹤立鸡群,赏月有了目无遮挡的好位置。众人于天台处,围席而坐,中间摆上月饼、葡萄、雪梨、柚子、葵瓜子、米饼,以及茶水。最先尝的定是父亲捎回来的月饼,两盒饼共八个,母亲麻利地将饼从盒子里统统拿出,拆除包装,手起刀落,一分为四,全然不顾我在旁,眼巴巴看着,目光里流转的乞求,哪怕给我留下一个也是好的啊,可母亲只给我留下她自己手中那一块。
待到席上吃食差不多都进了众人肚子的时候,父亲和大伯他们也聊完了田里庄稼,山头果树。虫鸣犬吠,像是归家的号角。大伙也终于站立起来,准备打道回府。那两个我心心念念的月饼盒子,最后落进了我伯娘和堂嫂的怀里。
经年之后,我记忆的土壤,许多旧物都被日晒枯,雨淋朽,风吹倒,慢慢了无痕迹。唯独年少时那轮圆圆的明月,十五夜和母亲走过的那段乡间小路,还有月下那张张被共度的好时光撑圆的脸庞,逆向生长着,随着岁月越是朝前,它们越发青葱葳蕤自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