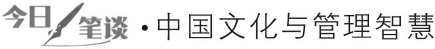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性善为人 仁义为政
潘永辉(市区)
孟子是先秦时期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关于其政治游历和管理思想,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云:“(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境贫困,靠母亲抚育成长。其母仉氏,生卒年不可考,以教子有方著称,留下了“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等家教佳话。孟子之家庭环境和一生经历,与孔子颇为相似,其本人对孔子也推崇备至,自云“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其思想学说继承并开新了孔子学说的微言大义,至唐代被韩愈列为接续孔子“道统”的关键人物,至元朝则被追封为“亚圣”,成为传统社会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圣人”,并称“孔孟”。
人性论问题是管理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对人性的看法不同,采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法也就不同。孟子是中国哲学史上性善论的代表人物。战国中期,人性问题成为诸家争鸣的一个焦点,有人(如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有人提出“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有人提出“有性善有性不善”论。而孟子则具体论证了他的“性善”观点:“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的性善论,在宋代以后,经过诸大儒的发挥,几乎成为传统社会共同遵奉的正统人性论,以至于幼儿启蒙教材《三字经》开篇即云“人之初,性本善”。这与西方文化从一开头就几乎认定人性为恶很不一样。细细推究,孟子提出性善说,除了受到中华先民“为善救世”的文化潜意识影响,与他母亲对他的良好的熏陶教诲更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中国民间早有说法: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现代心理学研究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一个人的家庭环境和童年经历,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对人的一生影响非常大。作为一个管理者,经常反省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反省自己精神世界的来历和走向,对走出某些心理定势和处世本能,尽量以善意去看待人事和从事管理工作,辩证地全面地看待宇宙人生,还是非常有帮助的。为人父母者,在家庭教育和家庭管理中,尽量多一些善的自觉性,对子女生活得阳光大度、积极向上还是很有益处的。
孟子由他的“性善论”,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仁政说”。他的“民本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非常有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如何处理好民生问题放在国家社会的首位,其次是社稷神灵问题,最后才是君王问题,这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和“仁者爱人”的态度是一致的。对于不合理的统治秩序和统治者,孟子也表现出一些“造反”精神:“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把商纣王这样的暴君称作独夫民贼,认为推翻他是合理的。这在“家天下”的私有制社会,还是难能可贵的。就算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对我们做好社会管理工作,反对大资本垄断民生和资本无序扩张,也是颇有启发的。民心向背的问题,是国家政治和社会(企业)管理中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一个国家社会、企业单位,如果管理者为民着想,大家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群策群力,那自然生活幸福指数高,事业大有可为。毛泽东也说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他们之间,是不是可以找到一点文化上的深层联系?“义利”关系问题也内涵在“仁政说”中。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有什么办法“以利吾国”,孟子则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国君问“利”,孟子答“义”,看起来南辕北辙,但是否有“利在义中”的可能?一个领导人、管理者,如果能自作示范,身先士卒,是可以带动集体道义的,如果事事与民争利,那老百姓就离心离德了。孟子甚至对君子士大夫的意志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的“义利”之辩,千百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对于我们端正生产经营的目的,把握好私利和公益的关系,还有着极大的启示。我们的生产经营,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还是为了个人贪得无厌的逐利之心?如何做到把商业行为的功利效用和社会效用统一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时代问题。总的来说,孟子的“仁政说”、“民本说”、“舍生取义”说,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国时代,与“务实”的法家学说比较,是显得比较“务虚”的,有点“理想主义”色彩,在当时也几乎没有君主接受。但是,后世的政治历史演变,却出现了有趣的现象:以草莽出身的刘邦当了汉皇帝,认为其天下乃“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而儒生陆贾却告诉他:“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刘邦醒悟,遂弃秦之“法治”而采用“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治国策略,“行仁义,法先圣”,倡导儒学,辅以黄老的“无为而治”,儒家由此逐渐取得传统社会官方管理哲学正统地位。而实际上,从历代统治者的管治手段看,“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儒表法里”也大有事实根据。儒家与法家,务虚与务实,相反相成,相互制约,相得益彰,不妨看作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吊诡之处或辩证之道。再加上道家的阴柔治术,大体上可以看作传统社会统治者管治哲学的“三角结构”,历代有出息的统治者,大都自觉不自觉地兼容运用之。
孟子的“尽心说”和“养气说”对管理者提升自我修养也很有借鉴意义。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性者,宇宙人生之本来面目,存心有诚,尽心无伪,则可领悟天性,明了“万物皆备于我”,天人合一,安身立命。而在领悟天性之前,有一个锤炼的过程,要由“小气”变得“大气”,要养出“浩然正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种“浩然正气”在人格上的体现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人生历练上的体现就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个良好的管理者,没有人格的修养和人生的历练是成就不了的。孟子本人理想高远,历练不少,所以他颇为自信:“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作为儒家圣贤,在“极高明而道中庸”中享受着“平凡人”的快乐:“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其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提醒我们要培养好管理接班人。
儒家政治哲学和管理思想发展到孟子阶段,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推行“王道”之中略有“霸气”,入世的色彩更浓,参政的主动性更强烈,提出的社会治理措施也更具体。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看,孟子的政治哲学和管理思想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也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苛求他具备今天的人民民主和群众管理观念,要看到他的思想观念为当代管理思想做出了文化精神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