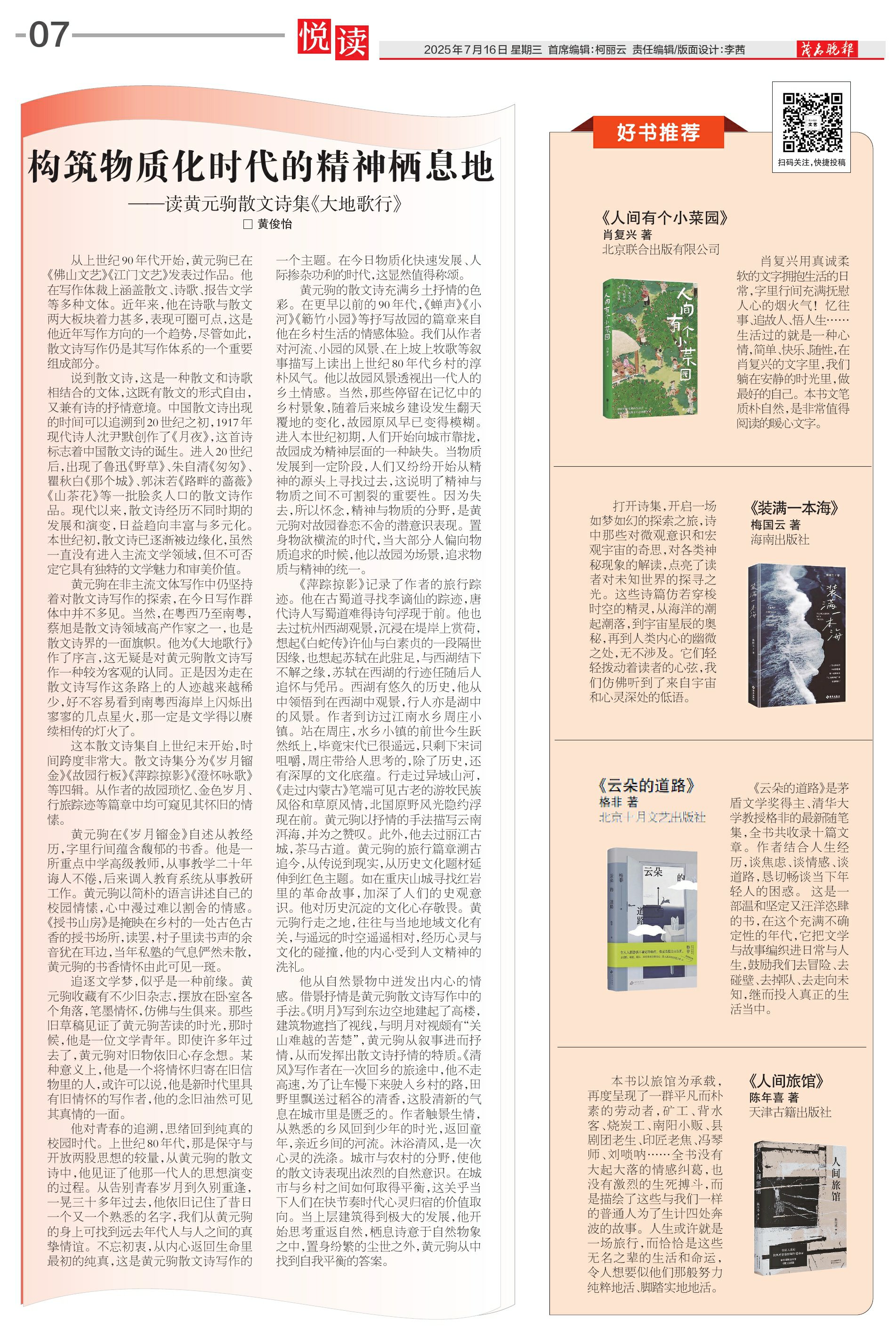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构筑物质化时代的精神栖息地
——读黄元驹散文诗集《大地歌行》
□黄俊怡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黄元驹已在《佛山文艺》《江门文艺》发表过作品。他在写作体裁上涵盖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多种文体。近年来,他在诗歌与散文两大板块着力甚多,表现可圈可点,这是他近年写作方向的一个趋势,尽管如此,散文诗写作仍是其写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说到散文诗,这是一种散文和诗歌相结合的文体,这既有散文的形式自由,又兼有诗的抒情意境。中国散文诗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之初,1917年现代诗人沈尹默创作了《月夜》,这首诗标志着中国散文诗的诞生。进入20世纪后,出现了鲁迅《野草》、朱自清《匆匆》、瞿秋白《那个城》、郭沫若《路畔的蔷薇》《山茶花》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散文诗作品。现代以来,散文诗经历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演变,日益趋向丰富与多元化。本世纪初,散文诗已逐渐被边缘化,虽然一直没有进入主流文学领域,但不可否定它具有独特的文学魅力和审美价值。
黄元驹在非主流文体写作中仍坚持着对散文诗写作的探索,在今日写作群体中并不多见。当然,在粤西乃至南粤,蔡旭是散文诗领域高产作家之一,也是散文诗界的一面旗帜。他为《大地歌行》作了序言,这无疑是对黄元驹散文诗写作一种较为客观的认同。正是因为走在散文诗写作这条路上的人迹越来越稀少,好不容易看到南粤西海岸上闪烁出寥寥的几点星火,那一定是文学得以赓续相传的灯火了。
这本散文诗集自上世纪末开始,时间跨度非常大。散文诗集分为《岁月镏金》《故园行板》《萍踪掠影》《澄怀咏歌》等四辑。从作者的故园琐忆、金色岁月、行旅踪迹等篇章中均可窥见其怀旧的情愫。
黄元驹在《岁月镏金》自述从教经历,字里行间蕴含馥郁的书香。他是一所重点中学高级教师,从事教学二十年诲人不倦,后来调入教育系统从事教研工作。黄元驹以简朴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校园情愫,心中漫过难以割舍的情感。《授书山房》是掩映在乡村的一处古色古香的授书场所,读罢,村子里读书声的余音犹在耳边,当年私塾的气息俨然未散,黄元驹的书香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追逐文学梦,似乎是一种前缘。黄元驹收藏有不少旧杂志,摆放在卧室各个角落,笔墨情怀,仿佛与生俱来。那些旧草稿见证了黄元驹苦读的时光,那时候,他是一位文学青年。即使许多年过去了,黄元驹对旧物依旧心存念想。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将情怀归寄在旧信物里的人,或许可以说,他是新时代里具有旧情怀的写作者,他的念旧油然可见其真情的一面。
他对青春的追溯,思绪回到纯真的校园时代。上世纪80年代,那是保守与开放两股思想的较量,从黄元驹的散文诗中,他见证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演变的过程。从告别青春岁月到久别重逢,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他依旧记住了昔日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名字,我们从黄元驹的身上可找到远去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谊。不忘初衷,从内心返回生命里最初的纯真,这是黄元驹散文诗写作的一个主题。在今日物质化快速发展、人际掺杂功利的时代,这显然值得称颂。
黄元驹的散文诗充满乡土抒情的色彩。在更早以前的90年代,《蝉声》《小河》《簕竹小园》等抒写故园的篇章来自他在乡村生活的情感体验。我们从作者对河流、小园的风景、在上坡上牧歌等叙事描写上读出上世纪80年代乡村的淳朴风气。他以故园风景透视出一代人的乡土情感。当然,那些停留在记忆中的乡村景象,随着后来城乡建设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故园原风早已变得模糊。进入本世纪初期,人们开始向城市靠拢,故园成为精神层面的一种缺失。当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又纷纷开始从精神的源头上寻找过去,这说明了精神与物质之间不可割裂的重要性。因为失去,所以怀念,精神与物质的分野,是黄元驹对故园眷恋不舍的潜意识表现。置身物欲横流的时代,当大部分人偏向物质追求的时候,他以故园为场景,追求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萍踪掠影》记录了作者的旅行踪迹。他在古蜀道寻找李谪仙的踪迹,唐代诗人写蜀道难得诗句浮现于前。他也去过杭州西湖观景,沉浸在堤岸上赏荷,想起《白蛇传》许仙与白素贞的一段隔世因缘,也想起苏轼在此驻足,与西湖结下不解之缘,苏轼在西湖的行迹任随后人追怀与凭吊。西湖有悠久的历史,他从中领悟到在西湖中观景,行人亦是湖中的风景。作者到访过江南水乡周庄小镇。站在周庄,水乡小镇的前世今生跃然纸上,毕竟宋代已很遥远,只剩下宋词咀嚼,周庄带给人思考的,除了历史,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行走过异域山河,《走过内蒙古》笔端可见古老的游牧民族风俗和草原风情,北国原野风光隐约浮现在前。黄元驹以抒情的手法描写云南洱海,并为之赞叹。此外,他去过丽江古城,茶马古道。黄元驹的旅行篇章溯古追今,从传说到现实,从历史文化题材延伸到红色主题。如在重庆山城寻找红岩里的革命故事,加深了人们的史观意识。他对历史沉淀的文化心存敬畏。黄元驹行走之地,往往与当地地域文化有关,与遥远的时空遥遥相对,经历心灵与文化的碰撞,他的内心受到人文精神的洗礼。
他从自然景物中迸发出内心的情感。借景抒情是黄元驹散文诗写作中的手法。《明月》写到东边空地建起了高楼,建筑物遮挡了视线,与明月对视颇有“关山难越的苦楚”,黄元驹从叙事进而抒情,从而发挥出散文诗抒情的特质。《清风》写作者在一次回乡的旅途中,他不走高速,为了让车慢下来驶入乡村的路,田野里飘送过稻谷的清香,这股清新的气息在城市里是匮乏的。作者触景生情,从熟悉的乡风回到少年的时光,返回童年,亲近乡间的河流。沐浴清风,是一次心灵的洗涤。城市与农村的分野,使他的散文诗表现出浓烈的自然意识。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如何取得平衡,这关乎当下人们在快节奏时代心灵归宿的价值取向。当上层建筑得到极大的发展,他开始思考重返自然,栖息诗意于自然物象之中,置身纷繁的尘世之外,黄元驹从中找到自我平衡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