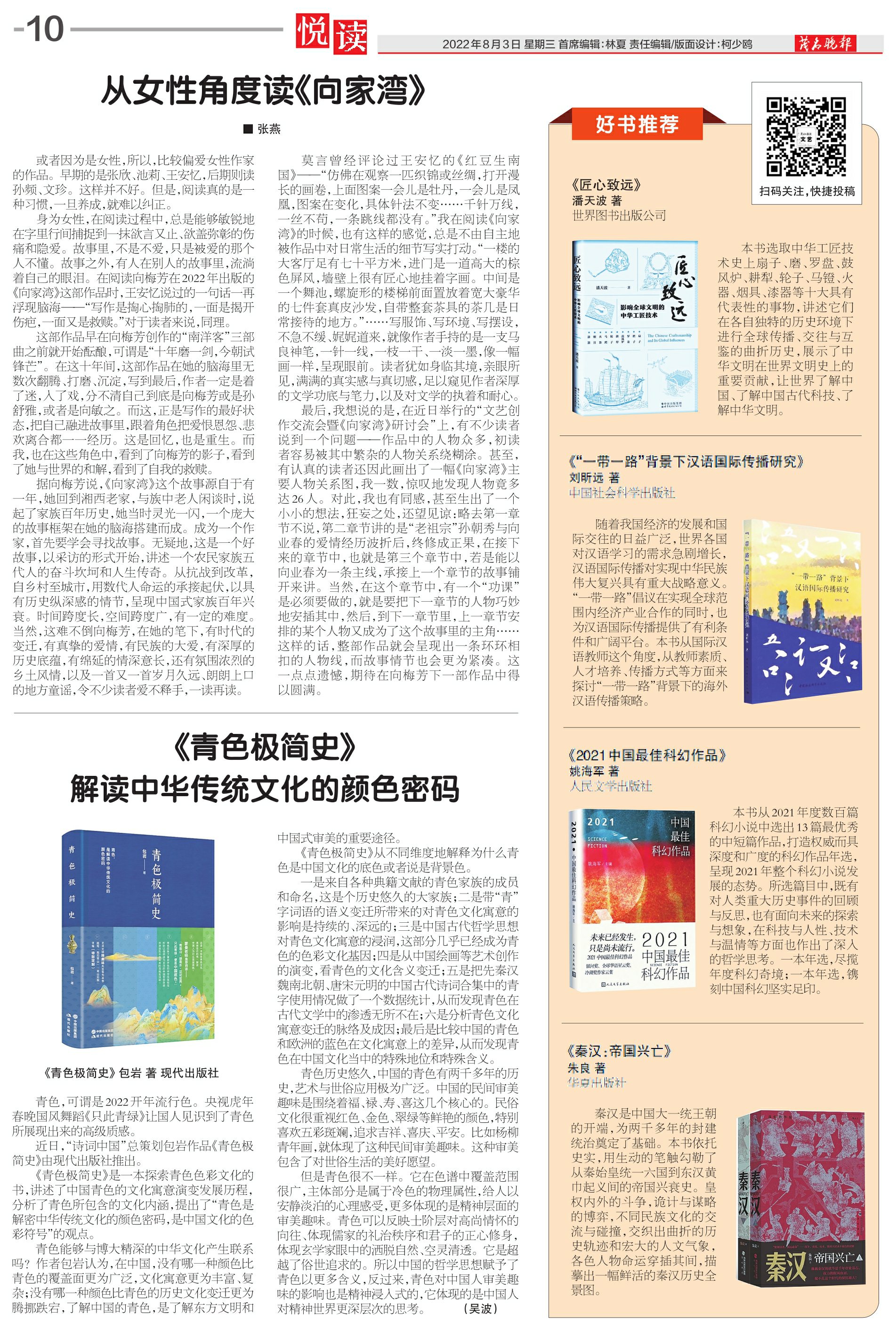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从女性角度读《向家湾》
■张燕
或者因为是女性,所以,比较偏爱女性作家的作品。早期的是张欣、池莉、王安忆,后期则读孙频、文珍。这样并不好。但是,阅读真的是一种习惯,一旦养成,就难以纠正。
身为女性,在阅读过程中,总是能够敏锐地在字里行间捕捉到一抹欲言又止、欲盖弥彰的伤痛和隐爱。故事里,不是不爱,只是被爱的那个人不懂。故事之外,有人在别人的故事里,流淌着自己的眼泪。在阅读向梅芳在2022年出版的《向家湾》这部作品时,王安忆说过的一句话一再浮现脑海——“写作是掏心掏肺的,一面是揭开伤疤,一面又是救赎。”对于读者来说,同理。
这部作品早在向梅芳创作的“南洋客”三部曲之前就开始酝酿,可谓是“十年磨一剑,今朝试锋芒”。在这十年间,这部作品在她的脑海里无数次翻腾、打磨、沉淀,写到最后,作者一定是着了迷,入了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向梅芳或是孙舒雅,或者是向敏之。而这,正是写作的最好状态,把自己融进故事里,跟着角色把爱恨恩怨、悲欢离合都一一经历。这是回忆,也是重生。而我,也在这些角色中,看到了向梅芳的影子,看到了她与世界的和解,看到了自我的救赎。
据向梅芳说,《向家湾》这个故事源自于有一年,她回到湘西老家,与族中老人闲谈时,说起了家族百年历史,她当时灵光一闪,一个庞大的故事框架在她的脑海搭建而成。成为一个作家,首先要学会寻找故事。无疑地,这是一个好故事,以采访的形式开始,讲述一个农民家族五代人的奋斗坎坷和人生传奇。从抗战到改革,自乡村至城市,用数代人命运的承接起伏,以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情节,呈现中国式家族百年兴衰。时间跨度长,空间跨度广,有一定的难度。当然,这难不倒向梅芳,在她的笔下,有时代的变迁,有真挚的爱情,有民族的大爱,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有绵延的情深意长,还有氛围浓烈的乡土风情,以及一首又一首岁月久远、朗朗上口的地方童谣,令不少读者爱不释手,一读再读。
莫言曾经评论过王安忆的《红豆生南国》——“仿佛在观察一匹织锦或丝绸,打开漫长的画卷,上面图案一会儿是牡丹,一会儿是凤凰,图案在变化,具体针法不变……千针万线,一丝不苟,一条跳线都没有。”我在阅读《向家湾》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总是不由自主地被作品中对日常生活的细节写实打动。“一楼的大客厅足有七十平方米,进门是一道高大的棕色屏风,墙壁上很有匠心地挂着字画。中间是一个舞池,螺旋形的楼梯前面置放着宽大豪华的七件套真皮沙发,自带整套茶具的茶几是日常接待的地方。”……写服饰、写环境、写摆设,不急不缓、娓娓道来,就像作者手持的是一支马良神笔,一针一线,一枝一干、一淡一墨,像一幅画一样,呈现眼前。读者犹如身临其境,亲眼所见,满满的真实感与真切感,足以窥见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与笔力,以及对文学的执着和耐心。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近日举行的“文艺创作交流会暨《向家湾》研讨会”上,有不少读者说到一个问题——作品中的人物众多,初读者容易被其中繁杂的人物关系绕糊涂。甚至,有认真的读者还因此画出了一幅《向家湾》主要人物关系图,我一数,惊叹地发现人物竟多达26人。对此,我也有同感,甚至生出了一个小小的想法,狂妄之处,还望见谅:略去第一章节不说,第二章节讲的是“老祖宗”孙朝秀与向业春的爱情经历波折后,终修成正果,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也就是第三个章节中,若是能以向业春为一条主线,承接上一个章节的故事铺开来讲。当然,在这个章节中,有一个“功课”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要把下一章节的人物巧妙地安插其中,然后,到下一章节里,上一章节安排的某个人物又成为了这个故事里的主角……这样的话,整部作品就会呈现出一条环环相扣的人物线,而故事情节也会更为紧凑。这一点点遗憾,期待在向梅芳下一部作品中得以圆满。